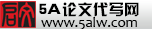在当代一些的国际统一实体法如罗马国际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委员会《欧洲合同法原则》等立法中,规定了合同上非财产损害的赔偿,1994年罗马国际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4·2条(完全赔偿)规定:“(1)受损害方当事人对由于不履行而遭受的损害有权得到完全赔偿。此损害既包括该方当事人遭受的任何损失,也包括其被剥夺的任何收益,但应考虑到受损害方当事人由于避免发生的成本或损害而得到的任何收益。(2)此损害可以是非金钱性质的,例如包括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其注释写道:“本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非金钱性质的损害也可赔偿。这可能是悲痛和痛苦,推动生活的某些愉快,丧失美感等等,也指对名誉或荣誉的攻击造成的损害。”“在国际商业中,本规则可能会适用于受雇于一个公司或一个组织的艺术家、杰出的男女运动员、顾问等人员签订的合同。”“对非特质损害的赔偿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采取何种形式,以及采取一种形式还是多种形式能够确保完全赔偿,将由法庭来决定。法庭不仅可以判给损害赔偿,而且可以命令其他形式的补救,例如在其指定的报纸上发布通告(对违反禁止竞争条款、重新开业、诽谤等等都可以发布公告)。”[33]
欧洲合同法委员会1996年《欧洲合同法原则》第9·501条(损害赔偿的权利)规定:“(一)受害方有权因对方当事人的不履行而造成的损失请求赔偿赔偿,只要该不履行没有依第3.108条而免责;(二)可获取损害赔偿的损失包括:(1)非金钱损失,和(2)合情合理地易于发生的未来损失” 规定了对非金钱损失(non—pecuniary loss)的损害赔偿[34]。
其他的统一国际私法国际公约也开始采用这种规定,例如《新华沙公约》草案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第16条规定:“一国发生在航空器上或在旅客上、下航空器的过程中的事故、造成旅客死亡、身体或精神伤害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旅客的伤亡完全是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法国民法典第1149条将侵权行为责任和合同责任予以包容,法律条文没有规定侵权行为与合同责任之区分[35]。判例和学说均承认非财产损害。对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法国法认为合同当事人不得将对方的违约行为视为侵权行为,只有在没有合同关系存在时才产生侵权责任[36]。法国最高法院一再宣称,侵权行为法条款不适用于合同履行中的过错行为[37]。日本民法第710条规定,因侵权行为致使财产上损害及非财产上损害者,被害人均得请求赔偿,日本之学说及其实务并类推适用于债务不履行发生之损害[38]。台湾民法关于债务不履行得否请求非财产损害赔偿无明文规定,史尚宽、王泽鉴、孙森焱、邱聪智等学者持肯定说[39]。荷兰新民法典在概念上将“财产损害及其他的不利益”作为应得到赔偿的损害,关于相当于“其他不利益”的非财产损害,只要是民法典上特别地承认,其恢复就应得到承认(以上,第6编第95条)[40]。
在英国,合同法上的非财产损害包括;一方面违反合同可能给对方造成不能用货币计算的损失(non-pecuniary losses)例如卖方交付一份有瑕疵的产品,结果造成对方购买者的人身伤害;更进一步,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给对方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折磨或烦恼。英国判例法表明对名誉造成的损害中对商誉损害可以在合同法上获得赔偿;以及在合同目的是提供安宁和快乐的享受、解除痛苦或烦恼、违法合同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直接造成的精神痛苦的三种情况下,可以给与精神补偿。[41] 美国合同法在违约同时造成了身体伤害,或者合同或违约系如此特殊以致严重精神损害成为一种极易发生的结果的情况下允许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42] 非财产损害明显的存在以致法院可以认为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预料可以导致这种损害时,法院就可以准许违约的受损害方获得此中非财产损害赔偿。沙利文诉奥康纳案件中,法官认为在违约之诉中,并不存在禁止此种赔偿的一般规则,这完全取决于合同的标的和背景,当医疗合同规定对原告实施手术时,当事人可能会期望在索赔是把精神的和肉体的伤害计算在内。[43]
四、我国的考察
按照以往通说,我国大陆现行立法在对违约能否请求非财产损害无明确规定,而予否定,通说认为,依法只应赔偿财产损失,而不包括非财产损害(因瑕疵履行造成人身损害时所引起的各项费用,也属于财产损失)[44]。但在学说上反对者不乏其人[45]。
我国这一规则散见于各种法律规定。《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产品责任是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的竞合,依法可以合同索赔因产品缺陷引起的非财产损害。有关旅行社的部门行政规章亦有因景点等与合同不符应予金钱赔偿的规定。旅客运输合同、医疗合同、劳动合同履行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有各部门规章规定的伤残补助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布后,韩世远先生扩大解释其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46] 认为该规定给法官“在裁判案件留下了很大解释余地……我国违约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可以根据这一条来处理”[47]。在司法实践上也不乏债务不履行的非财产损害赔偿,其中有较大影响、被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收录的“艾新民诉青山殡仪馆丢失寄存的骨灰损害赔偿案”、“马立涛诉鞍山事铁东区服务公司梦真美容院美容损害赔偿纠纷案”、“肖青、刘华伟诉国营旭光彩色扩印服务部丢失交付冲印的结婚活动照胶卷赔偿纠纷案”判决因为没有明却的法律依据,没有阐述和表明非财产损害赔偿与所涉及合同之间的关系[48]。但是1998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三模特与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画廊、广西人民出版社侵犯肖像权案件中,则明白地认定三被告违反招聘简章中保密的规定,违反了与原告达成的契约,因而判决三被告赔偿三原告非财产损失各一万元[49]。
契约法上的非财产损害问题与契约和侵权责任竞合制度有较密切相关,在《统一合同法》修订或《民法典》制定之前,在现实法律生活这个问题的法律适用须依赖于契约和侵权责任竞合制度责任。我国对于该制度,倾向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民法通则》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全国涉外、港澳台经济审判工作会谈纪要》第十二条有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责任竞合的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利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我国责任竞合的规定,对于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的人身权益的非财产损害,只要与契约有关联,可以依契约法调整,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施害人承担违约责任。
结 语
从法制发展史中考察,人类早期社会偏重于用侵权行为法来调整横向关系,契约的违反,也被视为侵权行为;至罗马法时期以降,因商品交换活动的频繁,当事人之间信赖增加,因而建立契约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契约关系逐渐扩张,与侵权行为法并峙,乃至侵蚀侵权行为法;近现代以来,若干原受侵权行为法约束的法律关系,例如缔约过失,加害给付等亦被视为契约关系,契约关系的效力,予以扩张适用。[50] 不少国家对于合同不履行而产生的非财产损害,亦有由侵权法向合同法的嬗变,与契约关系密切联系的合同当事人的人身关系以及其他非财产利益,随着交换活动的发达和合同关系的扩张,被纳入契约法的范围之中。许多德国学者称之为“侵权法向合同法的位移”[51]。因此,将与契约关联的非财产损害纳入契约法是民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
On Non-Property Loss Under Contract Law
Abstract: After brief introduce of non-property loss under contract relationship, the article constructs a trend that contract law is covering non-property loss and gives an idea of posing compensation into contract law, within the community between contract law and torts law and the explosion of contract relationship ,finally, Legal practice of China is researched .
key word: non-property loss contract law
contract relationship
------------------
[1] [2]孙森焱:《论非财产损害之赔偿》, 载郑玉波 刁荣华主编《现代民法基本问题》,东亚法律丛书,汉森出版社 1981年元月初版,第93页。
[]王利明先生说:“就违约损害赔偿来说,仅限于财产损失,不包括非财产损失。”参阅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
[3]如下文所述,近代以来,逐渐出现缔约过失、侵害债权(加害给付)、契约中的第三人等制度。
[4]申政武:《论人格权及人格损害赔偿》,《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第52页
[5]马元枢:《侵权行为与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责任范围》,载郑玉波、刁荣华主编《现代民法基本问题》,东亚法律丛书,汉森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年元月初版,第34以下。
[6]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347页。
[7]苏俊雄:《契约原理及实用》 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二页。
[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第46页。
[] 1870年,法国学者莫勒特在一本关于版权和工业版权的著作中论及人格权。1877年,德国学者加雷斯提出人格权的概念,但他把名誉、姓名、个人按其意愿安排生活的权利等划归知识产权。1907年柯尔勒在其著作中认为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属于著作权的内容。
[9]王利明、杨立新主编《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10]前引书。
[11]曾世雄:《损害赔偿原理》,三民书局1986年再版,第57页。
[12]王泽鉴:《时间浪费与非财产损害之金钱赔偿》,《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卷7,第139页。
[] “合理合法归我所有的东西与我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其他人未经我允许而使用它就会伤害我。”参阅[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越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梁治平校,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7页。
[13]业已商业化的约有隐私之公布权,参见宋克明:《英美新闻法制与管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形象权,参见董炳和:《论形象权》,《法律科学》1998年4月;广告权(美国法)、人物商品化权,参见沈达明:《知识产权法》,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49页以下;名人的姓名权,参见王利明、杨立新:《人格权新论》。
[14]石春玲:《期权定价与人身伤害赔偿》该文提出人身伤害的期权定价方法颇有启迪意义,《法学》1999年第9期。
[15]旅游服务合同按英
“纳入合同关系中的非财产损害赔偿提供各类毕业论文!”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著名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