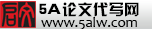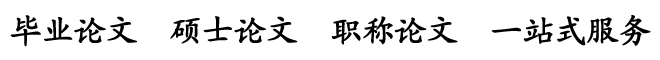|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学者和立法者对保险利益及其构成因素的不同观点,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分析了英国法环境下国际海运货物保险利益界定的弊端,建议我国确立以“风险承担”为界界定保险利益的法律模式;分析了承运人、提单质权人、保险人的保险利益;结合审判实际对实务中颇具争论的“保险利益的相对性”“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效力”和“保险利益与损失”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最后提出了立法建议。 [关键词]保险利益,国际海运货物保险,国际货物贸易,保险合同。 导言 是“赌博”,还是“合法地转嫁风险”,保险利益是唯一的试金石,百多年来人们对其总是争论不休,应该说这块“试金石”尚未定型。十七世纪英国很多人用保险来赌博,有的人明知自己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或不可能获取保险利益,但仍投保,并希望保险事故发生,保费就如下了小额赌注,保险事故发生了就可以获取一笔巨大的“彩金”,引致人们产生不良的道德观念。后来,人们意识到了赌博保险的危害性,便于1906年立法确立“保险利益”,禁止赌博保险,此后,关于保险利益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严格利益关系”与“广泛利益关系”的观点长期针锋相对,人们试图寻求一种“谁可以对特定的标的物购买保险”的合理和准确的认识,即对特定标的物具有什么关系的人才能购买保险,并在该保险标的出险时获得保险赔偿,但似乎这一目标仍未实现。 国际海运货物保险的保险利益 是主宰国际海运货物保险的灵魂,对此问题国内尚乏深究的基本理论,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很不完善,难以操作,无法形成准确、统一的理解。不同观点,见仁见智,差异颇大,已经带来许多困惑和负面影响,这一问题恐怕是我国海商立法的当务之急,值得探讨。 一、 保险利益的定义及其构成因素 (一)学者和立法者的认识 1.学者观点 (1)广泛利益关系说: a.1806年在英国发生的Lucena诉 Craudurd案中,英国法官Lawrence认为:对船、货有没有保险利益,应以“精神上确定的事”“真实的期待”或“与保险标的有某种利害关系”为标准。 b.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多数学者认为,如果某人与保险标的有关系、联系或者相关,使得其本人将会因为标的的保全而获得财务利益或者优势,或者因特定保险事故的发生而使标的破坏、终结、损害而蒙受财务损失,该人就具有保险利益 。 (2)严格利益关系说: a.前案中,英国法官Lord Eldon认为:保险利益是一种财产上的权利或者是因为财产订立的合同而产生的权利,在这两种情况下特定事件的发生可能使权利灭失并影响当事人的占有与利用。 b.杨良宜先生 认为:保险利益是指某人对于某种东西有法律上承认的权益,而且这种东西损失了,他就会因此而受到损害或引起责任。 c.司玉琢教授 认为: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与被保险财产之间依法产生或合法取得的经济上的利益,其损失的大小必须是能够用货币计算的。 d.汪鹏南教授 认为:保险利益是法律上认可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它独立于保险合同而存在。 (3)主体划分说: 英国有学者将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分为四类:被保险财产的所有人;向保险标的----货物提供担保,将钱借出去的抵押权人;保险人;其他能从航海冒险中获利的人,如代理人、承运人、留置权人等。 2.法律规定 (1)美国加利福尼亚洲保险法规定:“每种在财产中的利益,或者与财产有关联的利益或责任,其性质使得某种预期的灾难可能会直接损害被保险人,这种利益就是保险利益 。” (2) 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 (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下称MIA1906) 5(1), (2)规定:“保险利益是一个人与航海有利害关系,特别是当他与该航海或处在危险中的保险财产具有法律或衡平法的关系,如保险财产安全或按时抵达,他即能从中获益;如保险财产灭失、受到损害,或被滞留或引起有关责任,他的利益将受到损害。” MIA1906规定的保险利益因素: a.可取消的或未落实的保险利益,主要是指货物买方对未确定的货物具有保险利益。 b.保险风险,主要是指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风险进行再保险。 c.抵押权人接受船舶、货物的抵押而贷出的款项。 d.船员工资、预付运费和保险费。 从上述规定看,对海运货物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为货物的卖方、买方、保险人、货物抵押权人和承运人。 (3)我国《保险法》第11条规定:“保险利益 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我国海商法没有直接关于保险利益的规定,但第216条规定了海上保险合同的定义:“海上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对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和产生的责任负责赔偿,而由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的合同。”显然,该规定包函了保险利益的涵义。但国内立法没有任何关于保险利益构成因素的规定。 (二)评价与主张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有的人对保险利益的认识非常广泛,以“精神上确定的事”或“真实的期待”或“与保险标的有某种利害关系”作为保险利益的构成因素,表现为“广泛利益关系”的观点;有的则相对保守和狭窄,以“财产权和合同上的权利”作为构成保险利益的因素,表现出“严格利益关系”的观点;有的直接明确具体人,回避从漫无边际的“物的利益关系”角度认识的态度,表现出以“主体划分”的观点。美国立法者的认识比英国的立法者的认识宽泛得多,其只强调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形成经济利益关系,即仅要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经济利益” ,似乎已经摒弃了“严格利益关系”的观点。英国立法者吸收了“严格利益关系”与“主体划分”的观点,对保险利益的构成和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作出相应规定,它不仅要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经济利益”,而且还要求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或衡平法上的关系”,即“因所有权产生的权利”作为保险利益的构成因素。可见,美国与英国对保险利益的认识角度不同,理论各别,颇见歧异。我国立法者对“保险利益”的认识,基本上是借鉴英国立法者的观点,但比英国立法更为笼统。的确,过于“严格”的立法在实务中保险人很容易以“保险利益”为由抗辩而拒赔,不利于合理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过于“宽泛”的立法则给区分赌博保险和正当保险增加难度。 我们认为,过于“宽泛”的观点在实务中是不可取的,“宽泛”的标准,会导致有数不清的关系人对海运货物具有利害关系,他们都能满足“精神上确定的事”或“真实的期待”的标准,这样会造成无数的关系人对海运货物具有保险利益,并对货物进行投保,而期盼该货物出险而获得保险赔偿,显然,这与赌博没有什么区别。过于“严格”的观点也确实会限制正常贸易运作,而使得可以通过正当保险而转移风险的人们受到不应有的限制。“严格利益关系”说主张的保险利益因素是物权和债权,这有其合理之处,是可取的,但没有把承担的贸易风险作为保险利益的因素,这与当今国际货物贸易所有权与风险相分离的原则不符,可能是其不足,因为国际公约只界定货物风险的承担而不界定所有权的取得,即国际海运中的货物所有权是不明确的,而承担风险的界限则是明确的。“主体划分”说难以穷尽,而且各种关系人容易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其法律地位也可能随之改变,故此说恐怕难以涵盖具有保险利益的全部主体。 综上,我们认为,国际海运货物保险的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国际海运货物)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被保险人因该标的出险而损失或产生责任,该损失和责任受保险保障的经济利益。包括货物所有权、对货物的留置权,以提单设置的质权, 承担的货物风险和保险风险。可从下列五个方面进行把握: a.被保险人对货物有合法的利益。“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也就是依附在货物上的并被法律规范所认可的权利和承担的货物风险,这是获得保险保障的基础。尽管被保险人对货物有利益关系,但非法利益和仅对货物具有某种经济利益,是不能成其为保险利益的,是不能得到保险保障的。 b.货物出险会对被保险人造成损失或产生责任。保险合同是赔偿合同,目的是转移风险、对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人的损失进行补偿。如果货物发生保险事故并不会使被保险人造成损失或产生责任,被保险人就无保险利益可言。 c.受保险保障的经济利益。保险利益是保险赔偿的先决条件,没有保险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险保障,只有能通过货币形式计量的价值,才能获得保险保障。 d.保险利益是现实的经济利益。它不是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的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利益。 e.对国际海运货物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包括货物的卖方、买方、承运人、保险人和提单质权人等。 二、保险利益界定的法律模式 我们知道,贸易价格条件决定投保人,但投保并不表示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 各国的立法对国际贸易货物的所有权及风险转移的界限规定不一致。英国法实行货物风险随所有权转移而转移的原则,即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相统一。因此,在英国法环境下忽略“承担货物风险”作为保险利益因素,以所有权转移为界确定买、卖双方的保险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买方购买了货物保险,如遇货物出险,买方却因未获取提单、没有保险利益而不能获得保险赔偿,而卖方又因没有购买货物保险而受到损害,结果造成卖方不得不对提单未交付前的海运货物进行投保,这种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英国的模式不值得我们效仿。 我国现行法律对国际海运货物的保险利益的划分没有明确的界定,我们仅仅可以从我国法律大环境中领悟某种倾向。国内现行立法对国际贸易货物风险转移界限尚无明确规定,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对货物所有权的转移有具体规定,但对国际贸易货物的“交付”应当如何理解,司法实践中见仁见智。究竟以交付提单视为转移所有权?还是以交付货物转移所有权?究竟是在装货港将货物交给承运人视为转移所有权?还是在卸货港将货物交付给买方才视为转移所有权?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恐怕短时间内很难取得统一。我们认为,我国是《联合国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U.N.CONVENTION OF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下称U.N.CCISG)的缔约国,在其调整范围内对其法律原则和具体规定我们应当遵守和优先适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Terms,下称INCOTERMS )虽然是民间组织国际商会制订的,对一个主权国家无强制适用的效力,但其在国际贸易中普遍地得到承认和适用,我国也可以作为“国际惯例”予以适用。对此,我国《民法通则》有了明确的规定。 因此,在以我国法律为准据法解决国际贸易货物争议时,应当优先适用U.N.CCISG,并适用INCOTERMS 。 U.N.CCISG采取货物所有权与风险转移分离的原则,对货物所有权转移的界限没有规定。U.N.CCISG第67条规定:“如果销售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但卖方没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交付货物,自货物按照销售合同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转交给买方时起,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卖方授权保留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并不影响风险的移转。”而INCOTERMS 2000对CIF、CFR、FOB 价格条件下的解释是:买方必须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后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前者以货物“交付第一承运人”为界转移货物的风险,后者以“船舷” 为界转移风险,但两者均没有货物所有权转移的规定,仅明确风险转移。可见,U.N.CCISG与INCOTERMS 2000对风险承担界限的规定大致相同,但明显地与英国法“交付提单”作为所有权和风险转移的规定大相径庭。在所有权与风险转移相分离的原则下,即在只规定风险转移而不规定所有权转移的法律环境下,我们无法确定所有权转移的界限,那么,我们就只能根据“风险承担”来确认买、卖方对货物的权利与义务,而不能忽略“风险承担”作为保险利益的因素。因此,与U.N.CCISG和INCOTERMS 2000国际规范接轨,建立我国以“风险承担”作为保险利益构成因素,以风险承担的界线确定买、卖方保险利益的法律模式,应当成为我国目前执法的倾向和今后立法的取向。 三、海运相关人对货物的保险利益 (一)承运人的保险利益 承运人对其承运的货物有无保险利益?何时获得保险利益?是值得研究的。当然不能认为承运人在任何情况下对其承运的货物都具有保险利益,如果这样就会容易使承运人产生幻想,对其承运的货物投予小额的保费,并希望货物出现保险事故,以图获取巨额赔偿。在确定保险利益时,基本原则不能丢,那就是“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哪些是承运人依附在货物上的而被法律所承认的利益呢?我们认为,是承运人对货物的留置权。承运人常常根据运输和货物贸易的情况签发“到付运费”提单,这种提单的运费支付义务人为收货人。依据我国《海商法》第87条规定:“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有提供适当担保的,承运人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其货物。”该法第88条还规定:承运人留置的货物可以申请法院拍卖,用于清偿运费和相关费用。可见,在应当支付的相关费用没有支付时,法律赋予承运人有权对货物行使留置权和对留置的货物作出适当的处分。承运人对货物的留置权因货物的存在而实现,因货物的灭失而丧失,承运人的这种权益就应当视为被法律承认的利益。为保障承运人实现收取相关费用的权利,避免因货物的灭失、损坏而损害承运人收取相关费用权利,法律应当允许承运人对其承运的货物在相关费用范围内享有保险利益,换言之,承运人对货物的留置权具有保险利益,可以在相关费用的范围内对货物进行投保,一旦货物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向承运人作出赔偿。 承运人对货物留置权的保险利益,应从留置权形成之时起享有,但应当允许承运人在未获取保险利益时进行投保。 (二)提单质权人的保险利益 实务中,经常出现运输的航程需要一、二个月来完成,而提单则只需几天时间就可以到达买方的情况,为了融通资金,提单持有人往往将提单权利向银行出质以获取资金。我国《担保法》允许提单权利质押,并规定:以载明提货日期的提单出质的,提单提货日期先于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可以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提取的货物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出质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权利出质后,出质人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 从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提单出质后,出质人的权利已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提单权利已经成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质权人权利的客体,质权人已对提单权利享有了适当的处分权。由于质权人的债权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提单项下的权利,而提单项下的权利载体就是货物,质权人的质权会因货物完好到达而实现,也可能会因货物的灭失、损坏而丧失,因此,提单质权人对提单项下的货物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享有保险利益。为防患和转移风险并保障质权人实现其债权,提单质权人在其债权范围内对提单项下的货物投保法律应当予以准许。 我国《担保法》规定,以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 质权人对提单项下货物享有保险利益的时间应从其获取质权时起,即交付提单之日起。 (三)保险人的保险利益 保险风险由谁来承担,前人发明了再保险。MIA1906第9条第(1)项规定:“保险人对于所订海上保险契约,有着由其担负风险的保险利益,并可将其权益再保险。”我国《保险法》第28条规定:“保险人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以承保形式,部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的,为再保险。”可见,我国法律允许再保险。我国《保险法》第13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因此,保险人自保险合同成立后,在约定的保险期间的起点就承担了保险风险。这种保险风险随货物的风险产生而产生,同时又被法律所认可,理所当然,保险人对货物的保险风险享有保险利益,可在其保险风险范围内进行投保,同时我们应该从承担保险风险时起确定保险人获取了保险利益。 四、 保险利益及相关问题的争论 (一)保险利益的相对性 我国《保险法》第14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这是我国保险法对投保人的保险利益的绝对要求。这一要求对于不能转让的普通保险是可行的,但对国际海运货物的投保人是行不通的。如果把这一要求适用于国际海运货物的投保人,那么在FOB和CFR价格条件下,买方就必须在获得所有权或承担货物风险后才能购买保险。显然,这与国际货物贸易的实务是格格不入的。MIA1906,6(1),(2)规定:“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物发生损失时必须享有保险利益,尽管在订立保险契约时他没有取得保险利益的必要。…… 如被保险人在发生损失时对保险标的物尚未取得保险利益,则在其获悉损失发生后,就不得再以任何手段或方式,取得保险利益。”从英国法规定看,对国际海运货物保险的被保险人享有保险利益有相对的时间要求,我们称其为“保险利益的相对性”。国际海运货物保险的保险利益相对性与普通保险投保人的保险利益绝对性比较是其一大特点,其法律意义在于不要求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必须具有保险利益,但在保险标的出险时,保单持有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这一特点适应了国际货物贸易货物所有权和风险转移的特点,既为国际货物贸易实务提供了操作的便利,又使真正的利益关系人转嫁货物风险成为可能。可见,国际海运货物保险的保险利益相对性的法律和实践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对此尚无规定,或许已经造成了执法上的误区。 有这样一宗案例:国内A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生产五金铸件及五金制品,其与国外B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约定A公司以CFR价格条件向B公司购买一批钢材。A公司向保险人C公司投了海洋运输货物“平安险”。A公司在尚未获得货物的进口许可证之前,货物在开往国内港口途经日本海时因船舱进水,船、货沉没,货物全损。A公司持经B公司空白背书的指示提单和保单向C公司索赔,C 公司以A公司在货物出险时没有保险利益为由拒赔,引发诉讼。 诉讼中,双方围绕A公司尚未取得许可证在货物出险时有没有保险利益激烈争论,一审法院认为,A公司在货物出险时具有保险利益并判决A公司胜诉,C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A公司承担了货物的风险,理论上在货物出险时对货物具有保险利益,但由于A公司没有申领进口货物的许可证,违反了进口货物许可证管理的法律,因此,在货物出险时A公司对非法进口的货物不具保险利益。据此,改判A公司败诉。 我们认为,二审法院的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赞同二审法院“承担了货物的风险就对该货物具有保险利益”的观点,但不认为在货物出险时A公司没有领取进口货物许可证而使A公司丧失了对货物的保险利益。如何理解“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是争论的核心问题,归结为具体的问题就是:对未进入我国海关监管区域的货物尚未办理进口许可证是否构成非法进口?若构成非法进口是否A公司就丧失了法律承认的对货物的利益? 考察某人对某物是否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主要地应该考察人与物的关系,具体到本案来说,就是要考察法律上是否承认A公司对本案提单项下的货物形成了所有权关系,或法律上是否承认A公司对本案提单项下的货物承担了风险,而不能以考察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取而代之。就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即所谓的非法进口)而言,可分为走私行为和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根据我国有关法规规定,对这些行为可处没收货物、责令退运、罚款,应视具体情况由海关作出决定。 本案货物尚未领取进口许可证,应该如何定性?属行政法调整的法律关系,应依调整国家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法律去解决,我们不能抛开行政管理关系对相对人的行为进行定性。准确地说,应根据我国《海关法》规定的程序处理 ,具体程序为:海关作出处罚通知书并送达当事人,当事人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对行政复议不服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行政诉讼程序法院两审终审后才能定论(除非受处罚的当事人不提出行政复议、不提出起诉或上诉)。任何法院无权绕过法定程序对当事人涉及走私和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予以定性(绕过这些程序予以定性的行为本身就属违法),显然,没有经过适当的程序将运输途中沉没的货物定性为“非法进口”是不适当的。即便A公司的行为构成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10条规定:“ 违反国家进出口管理法规,没有领取许可证件擅自进出口货物的,没收货物或者责令退运;经发证机关核准补发许可证件的,处货物等值以下的罚款。”对A公司的处罚也只能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因为本案货物已沉没不可能作出没收或责令退运的处罚)。这种处罚是行政管理人对其相对人不符合行政管理法律规范作出的行政处罚,相对人对货物的所有权关系或承担货物风险的法定义务不因这种处罚而消灭(除非货物被全部没收),行政处罚本身并不否定相对人与物形成的法律关系,相对人原先被法律认可的对物的利益关系不因罚款处罚而丧失,很明显,在罚款处罚的情况下,认为A公司对该货物没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是不妥的。然而,本案运输中的货物仍在日本海,未进入我国海关监管的区域,从理论上讲A公司仍可对指示提单进行背书转让,甚至未必进口,没有进口就不可能构成走私或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因此,把运输中的货物定性为“非法进口”从而否定A公司对货物的保险利益恐怕是不妥当的。 (二) 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效力 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的效力关系紧密相联,可以这么说,没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是无效的保险合同。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1、2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我们知道,国际贸易的货物,特别是在FOB和CFR价格条件下,作为投保人买方,其在购买保险时往往对货物尚不具有保险利益。审判实践中,保险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常常以我国《保险法》有关保险利益的规定进行抗辩,认为投保人在投保时对货物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无须赔偿。 显然,实践中应解决二个问题:一是我国《保险法》有关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效力的规定能否适用国际海运货物保险;二是确定国际海运货物保险合同的效力以哪个时间作为基准考察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 我国《保险法》关于保险利益要求的规定,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当然,不可能这样理解:投保人投保时没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尔后获得了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有效),投保人对保险利益的有无,决定保险合同效力的有无,即投保人没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当然无效,投保人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不一定有效。显然,这一规定不能适应国际海运货物保险,因为国际海运货物的投保人在CFR和FOB价格条件下,买方在货物买卖合同签订后,货物装船前往往会购买货物保险,此时,作为买方既没有货物的所有权也没有承担货物的风险,当然对货物没有保险利益,但实务中不可能要求买方获取保险利益后才去购买保险,在未承担货物风险或取得所有权以前买方购买保险不但合理,也为国际货物贸易所必要。可见,由于国际海运货物保险合同可转让的特性,不能简单地以投保人没有保险利益视保险合同为无效,应在转让和保险事故发生时去考察让与人和受让人对货物是否具有保险利益,进而决定合同效力。投保人购买保险时可以没有保险利益,此时不能视合同为无效,而是存在效力待定情况,如果买方在保险合同转让和保险事故发生当时获取了保险利益,其订立或受让的保险合同就有效,如果其签订保险合同后对货物一直没有取得过保险利益,或受让的保险合同本身就不具保险利益,那么,该保险合同属无效。因此,我们认为,片面地理解投保人没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是不妥和不符合实务要求的,以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国际海运货物保险合同的效力是有害的。 (三)保险利益与损失的关系 有这样一宗案例,A公司作为一批钢材的卖方在俄罗斯远东港口将该批钢材装上了船舶,承运人向A公司签发了空白指示提单,中间商B公司与A公司签订了该批钢材的买卖合同 ,B公司又与C公司签订了该批钢材的买卖合同,价格条件为CFR汕头,C公司作为买方就该批钢材向D公司投保了平安险,在航行途中因货舱进水导致船、货沉没,因信用证过期的原因,A公司未能通过信用证实现结汇,遂将提单空白背书转给B公司,B公司又空白背书转给C公司,货物沉没后C公司没有向B公司支付货款,C公司遂书面声明将提单和保险合同下的权利让与给B公司,B公司也未向A公司支付货款,B公司持保险合同和提单向保险人D公司要求索赔,D公司以B公司没有支付货款,保险事故没有造成B公司损失为由拒赔,B公司向法院起诉D公司。诉讼中D公司以同样的理由进行抗辩,一审法院支持了B公司的赔偿请求。二审法院则否定了B公司的赔偿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保险合同的赔偿性原则,索赔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实际损失确实存在,即使保险事故造成了保险标的的灭失,如果被保险人并没有因此而遭受经济上的损失,保险人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这里就存在一个损失衡量的标准问题,究竟是以被保险人支付了货物的对价作为衡量其损失的标准呢,还是以被保险人有无保险利益作为衡量其损失的标准。 我们认为,C公司自货物越过船舷起就承担了货物的风险,C公司在货物发生保险事故时对船载货物具有保险利益是无庸置疑的。为什么要考察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说穿了就是要研究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是否对被保险人造成了损失或产生责任,说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而又认为他没有损失是荒谬的。事实上,保险利益体现的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会给被保险人造成损失或对被保险人产生责任。正如确定了甲对特定的物是所有权关系,该物受损,毫无疑问损失肯定是甲的,甲取得该物所有权时是否支付了对价则无须进行考证。因此,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就发生了损失或产生了责任。有无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纠纷中保险人是否赔偿的前提,但确定了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后,就不能支持保险人关于被保险人不存在实际损失的抗辩理由。在保险合同纠纷中保险人赔偿的条件是: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具有保险利益;保险标的发生了保险事故;在保险责任期间、属保险人承保的责任范围;不存在保险人免赔的情况。符合上述条件,再去考察被保险人有无实际损失,或者把被保险人有没有支付货物的对价作为赔偿条件实属节外生枝。从民法的基本原理可知,合同是债发生的原因,货物贸易合同一旦签订,并合法有效,合同之债就已确定,即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确定,并不因为买方是否支付货款而改变。换言之,买方没有支付货款并不影响货物所有权转移及货物风险的转移。所谓国际贸易的风险转移就是货物灭失、毁损的风险何时起从卖方转移买方。在卖方依约将货物交给承运人后,运输途中发生货物灭失、毁坏,不能免除买方支付货款的义务。因此,当发生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损失时,承担了货物风险的买方(被保险人)对该保险标的物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事故造成的保险标的的灭失或损坏用金钱予以衡量就是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U.N.CCISG,第66规定:“货物在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后遗失或损坏,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除非这种遗失或损坏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本案中,承运船舶在运输途中货舱进水沉没,导致货物全损,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毫不相干。因此,根据该规定不能解除买方C公司向B公司,B公司向A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显然,买方(被保险人)支付货款的义务是存在的。总之,认为买方尚未支付货款,就没有损失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保险利益原则,也与民商法基本理论相悖,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保险利益的有无是保险人赔与不赔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被保险人是否存在损失或产生责任的标准,决不能以“是否支付货物价款”去判断被保险人损失的有无,进而判断保险利益的有无。保险利益与损失正确的逻辑关系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存在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如承担了货物风险、取得货物所有权等)----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会给被保险人造成损失或产生责任)----保险人赔偿;而不是:被保险人支付货款(造成被保险人损失)----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保险人赔偿。 五、立法建议 综上讨论,建议在我国《海商法》“海上保险合同”一章内作如下规定: 1.国际海运货物保险的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国际海运货物)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被保险人因该标的出险而损失或产生责任,该损失和责任受保险保障的经济利益。包括货物所有权、对货物的留置权、以提单设置的质权、承担的货物风险和保险风险。货物的卖方、买方、承运人、保险人和提单质权人可以成为保险利益的主体。 2.货物在装船前交给承运人的,卖方承担交付第一承运人之前货物的一切风险;买方承担交付第一承运人起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货物在装船时交付给承运人的,卖方承担越过船舷前货物的一切风险;买方承担越过船舷起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承担风险一方自承担风险时起对货物具有保险利益。 3.投保时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不必具有保险利益,但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未获取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试图取得保险利益的任何行为均属无效。已证明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时,被保险人以其没有实际损失的抗辩不成立。 结束语 本文对国际海运货物保险的保险利益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由于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层面既多又杂,而且在实务中颇具争论,上述探讨仅仅是一个开始,远不能解决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研究仍有待继续深入。应当清醒认识,国内在这些方面的立法很不完善,尤其《海商法》作为调整海运货物保险的特别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定几乎空白,这与我国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的国际货物贸易和相关的货物保险很不相称,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将更加迅猛,国际货物贸易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海运来完成的,而国际海运货物保险与国际货物贸易密切相连,这就使得法律规范需求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因此,本文的初步探讨若能引起有关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立法的关注,当为最大心愿。 参考文献 1.翟莉译:《保险利益定义》,《海事司法论坛》2000年第4期。 2.杨良宜:《航运实务丛谈之五---海上保险》,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3.E. R. Hardy Ivamy: Marine Insurance, Third Edition. 4.Glame Robert:《Marine Insurance》,《海上保险资料》,西南政法学院国际法教研室编。 5.司玉琢:《新编海商法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 6.汪鹏南:《海上保险合同法详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 7.杨文贵:《“保险利益”还是“经济利益”》,《中国海商法协会通讯》第48期。 8.孙美兰:《论国际货物买卖中货物损失风险的转移》,《民商法论丛》第8卷。 9.朱奇武等:《国际贸易公约与惯例》,法律出版社1994年。 10.进出口业务编写组:《国际贸易法律惯例规则选编》,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 11. 左晓东:《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释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12.林国民等:《外国民商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 Insurable Interest of International Marine Cargo Huang Weiqing (Guangzhou Maritime Court) Abstract:This article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ome different views of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nd legislators as to insurable interest and its constituents, puts forth some unique view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to define the insurable interest under the backgrounds of English law, then suggests our country to adopt the legal mode to define insurable interests by the assumption of risk. This article also analyses the insurable interests of the carriers, the pledgee of B/L and the insurer,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vity of insurable interest, the relation between insurable interest and validity of insurance contract, and between the insurable interest and loss, together with some problems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sets forth the personal views of the author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gives suggestion to perfect the legislation of our country in this respect. Key words: insurable interest, international marine cargo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goods, insurance contract. |
“国际海运货物保险的保险利益提供各类毕业论文!”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著名出处。